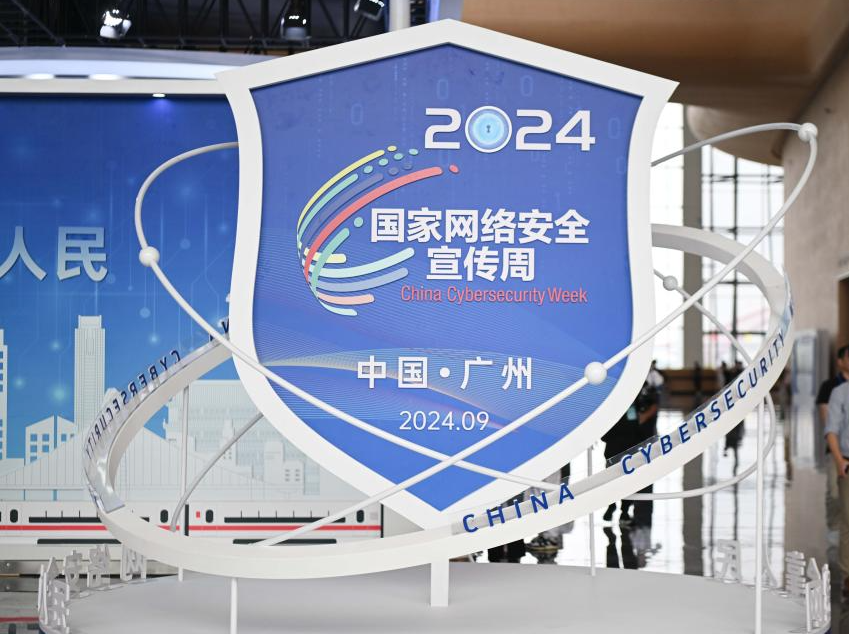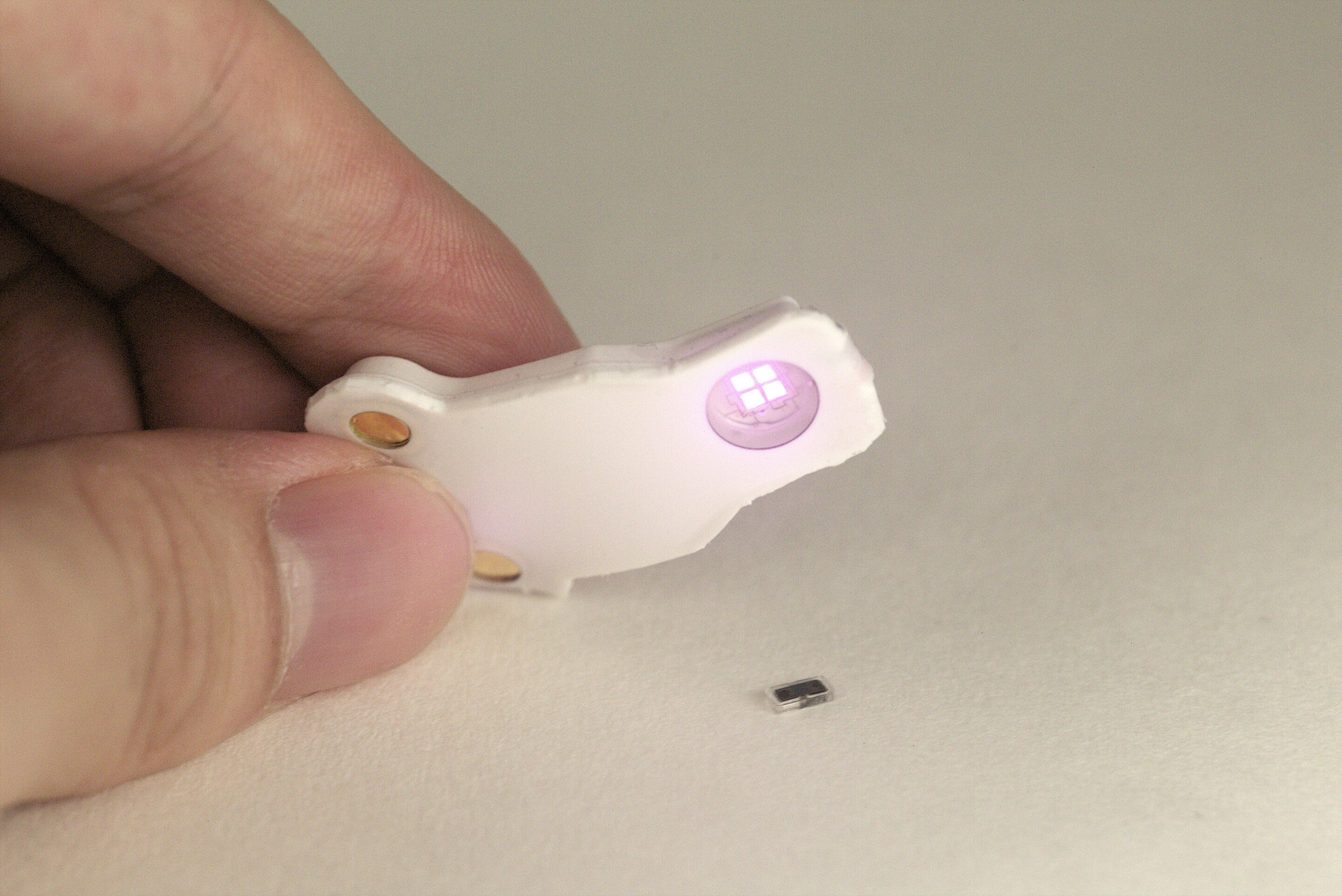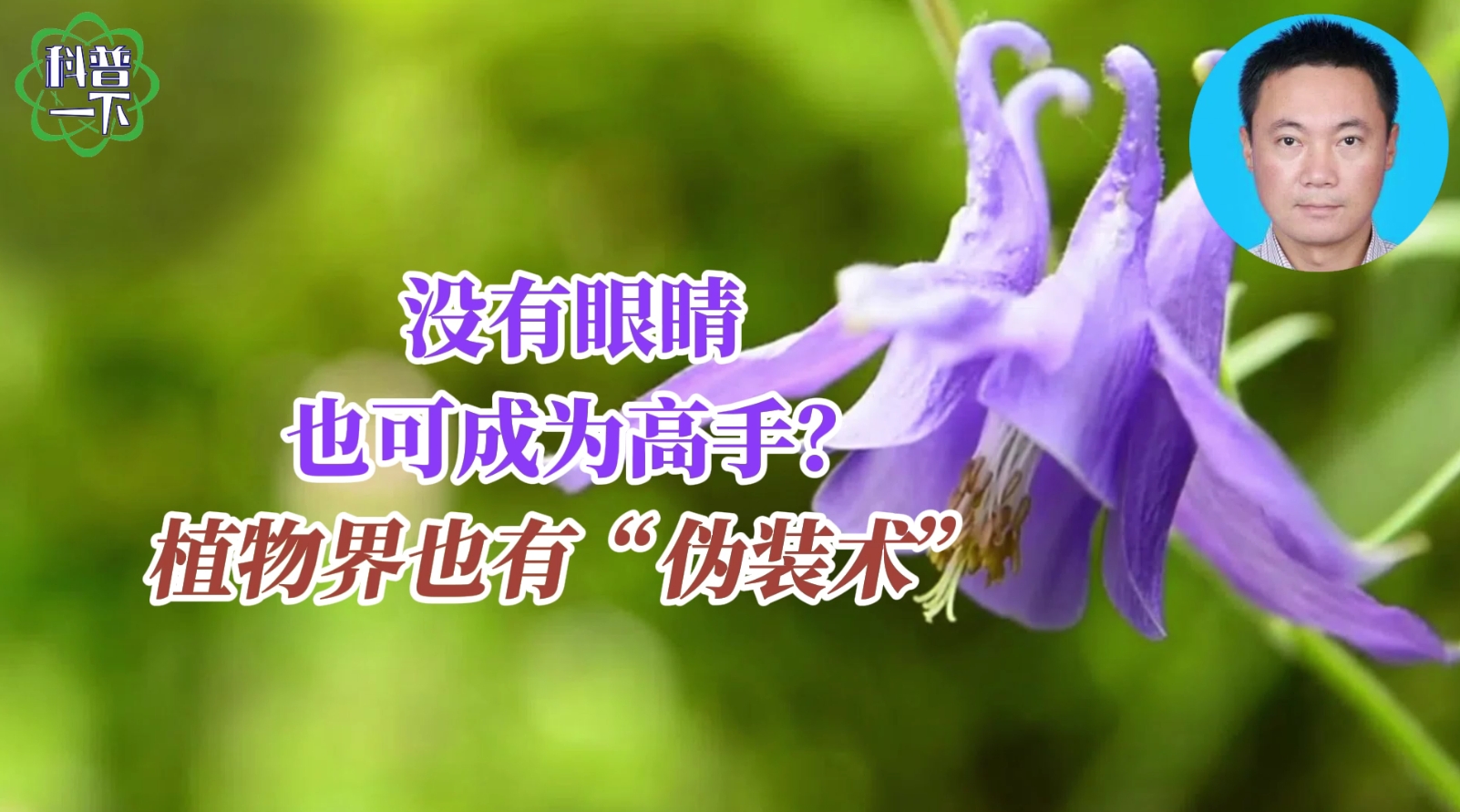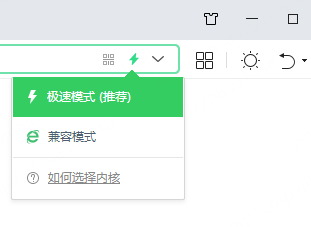九曲黃河萬里沙。在黃河“幾字彎”的“豎彎鉤”上,一座大型水利樞紐工程即將拔地而起,成為繼小浪底水利樞紐工程之后的又一大型治黃戰略性工程。它就是古賢水利樞紐工程。
九曲黃河萬里沙。在黃河“幾字彎”的“豎彎鉤”上,一座大型水利樞紐工程即將拔地而起,成為繼小浪底水利樞紐工程之后的又一大型治黃戰略性工程。它就是古賢水利樞紐工程。
前不久,生態環境部批復古賢水利樞紐工程環境影響報告書,標志著古賢水利樞紐工程開工所需的前置要件已全部辦結,為工程立項及年內開工建設奠定了基礎。
古賢水利樞紐工程是黃河水沙調控和防洪減淤體系的關鍵工程,先后被列入國務院確定的172項和150項重大水利工程清單、《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102項重大工程。
近日,古賢水利樞紐工程設計總工程師、黃河實驗室總工程師張金良接受了科技日報記者的采訪,講述他帶領團隊升級黃河水沙調控“開關”的艱辛歷程。

在“千層餅”上建設大壩
記者:您能否簡要介紹一下古賢水利樞紐工程。
張金良:古賢水利樞紐工程位于黃河中游北干流磧口至禹門口河段,建成后可以控制黃河73%的水量、60%的沙量和80%的粗泥沙量。它是黃河歷次重要規劃確定的干流七大骨干樞紐之一,在黃河保護治理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該工程的開發任務是“以防洪減淤為主,兼顧供水、灌溉和發電等綜合利用”,設計總庫容133億立方米,其中調水調沙庫容35億立方米,是世界紅層地基上建設的最高碾壓混凝土重力壩,總投資600多億元。
記者:自古以來,黃河都被稱作“地上懸河”。如今,這個情況有所改變嗎?
張金良:1999年以前,黃河下游河道年均淤積泥沙2億噸,河床高度每年因泥沙淤積抬升5公分至10公分。小浪底水利樞紐工程運行以來,黃河下游的泥沙淤積情況得到了一定的緩解,但形勢依然嚴峻。
當前,黃河下游河道“地上懸河”長度達800公里,下游河床平均高出背河地面4米至6米,其中河南省新鄉市河段高于地面20米。
黃河一旦決口,決堤洪水或漫延黃淮海平原12萬平方公里,影響1.3億人口,是中華民族不能承受之重。
記者:古賢水利樞紐工程對扭轉這個局面可以起到怎樣的作用?
張金良:目前承擔黃河調水調沙任務的,主要是位于中游的小浪底水利樞紐工程。但該工程的排沙動力不足,攔沙庫容非常有限,下游河道泥沙淤積風險依舊較高。而古賢水利樞紐工程建成后,其將與小浪底水利樞紐工程聯合運行,進一步減少黃河下游河道泥沙淤積量,可確保在百年內黃河下游河床不抬高。
記者:古賢水利樞紐工程建設地的自然條件如何?
張金良:古賢水利樞紐工程所在地地下巖土結構比較特殊,是由粉砂巖地層、長石砂巖地層和粘土巖地層等組成的。這些地層有的軟、有的硬。形象地說,它就像一張由軟硬不一的巖石層堆疊起來的“千層餅”。
地層軟硬相間非常影響地上建筑的穩定性。古賢水利樞紐工程是高壩大庫,是國內外紅層地基上壩高最高的混凝土重力壩。要在這樣軟硬相間的紅層地基上建一座巨型大壩,且讓其從容應對巨大的水推力和泥沙壓力,就像是在一塊坑洼不平、滿是石子砂礫的土地上蓋一座抗風抗震的摩天大樓。這對工程設計者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挑戰。
記者:這個難題您和團隊成員是如何解決的呢?
張金良:我們首先用直徑為1米的大口徑鉆頭,進行了累計長度超過600米的河底探洞。其次,利用自主研發的泥化夾層高品質取芯關鍵技術,我和團隊在河床布置了上百個鉆孔,探明了泥化夾層空間分布和結構特征。最后,我們采用空地融合數字化勘察技術,為描繪這張“千層餅”研發了數學模型,為工程設計提供了堅實的支撐。在此基礎上,我們聯合多家科研和設計單位,設計出多個方案并進行反復比選,最終決定采用淺層挖除、中層齒槽截斷、深層(深部軟弱夾層)“掏空”置換并結合壩后蓋重綜合抗滑穩定措施,有效解決了紅層地基上超高混凝土重力壩建設難題。
記者:把相當面積的深部軟弱夾層“掏空”,這聽起來是個大工程。
張金良:沒錯。深部軟弱夾層分布在河床下約60米處。在這樣的深度上,我們需要先打施工支洞,然后橫向沿著夾層挖洞、掏空。這絕非易事。之后,我們還要把混凝土灌填到洞中。
此時,我和團隊需要時刻關注灌填是否密實、會不會出現空隙等問題。千里之堤,潰于蟻穴。這些被灌填的地層未來是要承載水利工程的,任何細節上的疏忽都可能造成極大的損失。
從“蓄清排渾”到“蓄清調渾”
記者:除了在建設方面,古賢水利樞紐工程在設計運用上有哪些創新?
張金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多沙河流水利樞紐工程設計運用方式經歷了從“蓄水攔沙”到“蓄清排渾”“蓄清調渾”的演化過程。打個不太準確的比方,1960年建成的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是黃河水利樞紐工程設計運用技術的1.0版本(“蓄水攔沙”),1999年建成的小浪底水利樞紐工程是2.0版本(“蓄清排渾”),而即將開工建設的古賢水利樞紐工程是3.0版本(“蓄清調渾”)。
記者:2.0版本和3.0版本有何區別?
張金良:所謂“蓄清排渾”,就是設置專門的排沙期和適宜的排沙設施,以清除水庫泥沙。而“蓄清調渾”是指設置合適的攔沙和調水調沙庫容,通過“攔、調、排”全方位協同調控,實現有效庫容長期保持和部分攔沙庫容的再生利用、攔沙庫容與調水調沙庫容一體化使用。
從“排”到“調”,別看二者只有一字之差,這其中卻涉及諸多關鍵技術突破。過去幾十年的“蓄清排渾”過程中,由于水庫調節庫容有限,水庫泥沙內調能力不足等問題逐漸顯露。而這些棘手的問題,都要在“調”的時候解決。
記者:具體是怎么解決的呢?
張金良:在“蓄清調渾”運用方式下,水庫調水調沙的靈活度將得到大幅提升。在來沙較多時,水庫可以降低水位至死水位以下敞泄排沙,突破原來單一泥沙侵蝕基準面設計,形成雙泥沙侵蝕基準面;在來沙較少、來水較豐時,水庫則可以進行水量跨年調節。如此一來,水庫的攔沙庫容和調水調沙庫容可以實現互換,“沙多調沙、沙少調水”,有效增強了水庫的功能性。此外,我們還運用自主研發的“三槽”淤積形態和庫容分布耦合設計技術破解了庫區泥沙淤積難題。
與此同時,我們還在壩型選擇、樞紐建筑物布置等方面進行了系列創新,解決了壩前灘面高程高、泥沙淤積厚度大等系列問題,確保工程安全運行。
記者:可以感受到,從“蓄清排渾”到“蓄清調渾”,一字之差其實蘊含了非常多的巧思。當初,您和團隊是怎么想到這個新辦法的呢?
張金良:我們團隊主要是圍繞問題去思考解決辦法。遇到問題,我們首先去分析問題、再想辦法去解決,最后研究出新技術。“蓄清調渾”運用設計思路,也是在解決過去多泥沙河流水庫出現的問題時,我們想到的。在建設新的水利樞紐工程時,我們必須創新技術手段去解決難題,這樣建設的工程才有意義。
記者:從想法到實踐,這中間還是有很長的路要走。
張金良:是的。“蓄清調渾”從最初提出想法到得到數學模型、進行物理模型驗證,我們花了近10年的時間。其間,我們要解決大壩開洞位置、大壩水流流速、邊壁磨損控制等諸多問題。而解決它們不僅需要復雜的計算,還需要很多專業人員的配合。我們先后與許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展開合作,在經歷了無數次的計算、試驗和調整后,才有了現在的古賢水利樞紐工程建設方案。
記者:古賢水利樞紐工程建成后,將帶來哪些改變?
張金良:古賢水利樞紐工程建成后,將輔助小浪底水利樞紐工程,提升其調水調沙后續動力,并在減輕下游河道淤積、推動水資源節約集約利用、生態環境保護治理和流域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在提升小浪底水利樞紐工程調水調沙后續動力方面,古賢水利樞紐工程建成后可以提供35億立方米的調水調沙水量,為小浪底水利樞紐工程排沙和下游河道輸沙提供充足的水流動力條件。
把論文寫在大江大河上
記者:治理黃河需久久為功,更需薪火相傳。
張金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老一輩科技工作者立志消滅黃河水患,先后采取加高大堤、修建水利工程等措施,力保黃河不改道、不決口。幾十年后,新一代“治黃人”探索創建了黃河調水調沙理論和技術,并依托科技力量構建了“原型黃河、數字黃河、模型黃河”的“三條黃河”體系,將黃河的研究與治理提上了新的高度。
一代又一代治黃前輩為黃河保護治理付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才有了如今黃河歲歲安瀾的歷史奇跡。現在,治黃的接力棒正在傳遞給更為年輕的下一代,期待他們能作出更大的貢獻。
記者:的確,年輕的力量代表著黃河治理的未來。能否介紹一下您的團隊?
張金良:在我們的團隊中,像我這樣50歲以上的人員大概只占到5%,大部分都是“80后”“90后”。這些年輕人基本都來自“雙一流”高校,擁有碩士以上學位,擁有博士學位的占一半。可以說,這是一支既有青春活力又有科研素養的隊伍。
記者:您的團隊是如何發揮“傳幫帶”作用培養年輕科技工作者的?
張金良:一方面,團隊中的資深專家會時刻提醒年輕隊員及時發現問題、正確認識問題、積極解決問題,做到“授人以漁”;另一方面,團隊有良好的學習氛圍,比如我們有一個名為“青年沙龍”的學術聚會。在“青年沙龍”中,大家可以暢所欲言,就學術問題展開激烈討論。
同時,我們始終秉承“絕知此事要躬行”的理念,堅持一切從實踐出發,鼓勵年輕人下工地、參與具體的工程項目設計,把論文寫在大江大河上。一般來說,新進人員工作不超過5年,就可以成長為業務骨干。
記者:未來,您和您的團隊將在哪些方面繼續開展攻關?
張金良:治黃百難,唯沙為首。我們目前在做的,是要研究出一套包含干支流的全黃河調水調沙技術理論體系。今年,我們已經出版了《黃河泥沙工程控制論》,其理念是用系統論的方法從入黃泥沙、水庫泥沙、河道泥沙、河口泥沙等方面整體管理全黃河的泥沙,為新時期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提供重要的技術支撐。
記者手記
與張金良對話,感覺就像在春天里漫步。張金良說話慢悠悠的,遇到難解釋的問題,他習慣性地先頓一頓再說。滔滔黃河,在他口中,好像變成了“涓涓細流”,流淌進記者的心里。從一個專業術語到一段治河的歷史,從一段復雜的技術原理到未來的學術研究方向,他都說得恰到好處。
張金良的辦公室里有一張很大的黃河流域全圖,干流支流、地勢地貌、大大小小的水電站,一圖盡覽。站在這張圖前,他常常若有所思。
張金良說,黃河千年水患,到他們這一代一定要想辦法解決掉。“我們要用系統的、全域的思想去管理黃河。這是我們已經著手在做且會一直做下去的事情。”他說。
治理黃河已經成為張金良生命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他的頭發已經半白了,但每天仍像團隊里的年輕人那樣熬夜工作,更喜歡和“90后”們一起搞科研。
中國的治黃史是一部奮斗史,一部調查研究史,一部需要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書寫的歷史。黃河治理是一條漫漫長路,張金良說自己依舊在路上,還要走得更遠。
(科技日報記者 孫越)